5月14日,尼日利亚女作家阿比·达蕾(Abi Dare)的小说《故我咆哮》(And So I Roar, 2024)以一种“咆哮”的姿态挺进英国海伊文学节(Hay Festival)首届长篇气候小说大奖的短名单,并击败包括布克奖获得者《轨道》(Orbital, 2023)和迈尔斯·富兰克林奖获得者《值得赞扬》(Praiseworthy, 2023)在内的多部作品,一举夺魁。达蕾因此可以获得1万英镑的奖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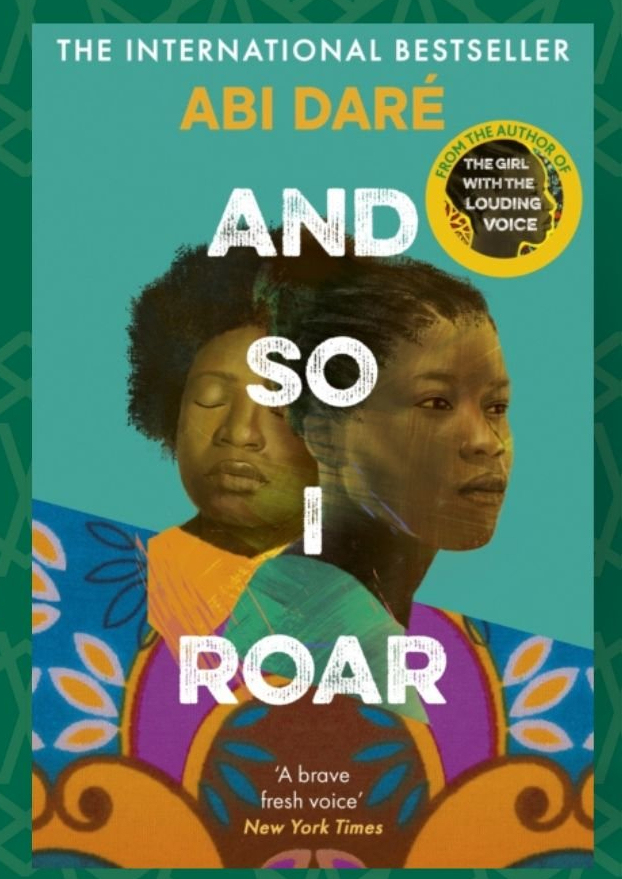
《故我咆哮》英文版封面
这是全球南方气候小说的一次完胜,彰显政治正确的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气候变化如何加剧全球南方性别的不平等?全球变暖时代,非洲的童婚和奴隶制还存在吗?全球南方被“贱斥”(abject)、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就环境问题发声吗?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也就构成了小说中的全球南方女性主义生态政治学。

阿比·达蕾获奖照片,来源:https://climatefictionprize.co.uk
《故我咆哮》是达蕾前一部畅销小说《大声说话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Louding Voice, 2020)的续作。在《大声说话的女孩》中,14岁的尼日利亚乡村女孩阿杜尼被爸爸卖给近60岁的邻村出租车司机莫鲁弗,成为他的第三位妻子。夫妻四人连同第一位妻子的女儿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莫鲁弗的第二位妻子卡蒂嘉死于情人家门口的河边,阿杜尼则被误认为是凶手。为躲避村人的追捕,阿杜尼通过人贩科拉,从伊卡迪村逃到大城市拉各斯,到莫鲁弗的第一位妻子弗洛伦斯家当女仆,每天只被允许吃一餐饭,受尽各种暴力凌辱,是非洲新奴隶制中被剥削压迫者的典型。这位14岁的女孩凭借乐观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在辛苦劳作的间隙,到弗洛伦斯家书房里偷偷学习英文,最后在厨师科菲和邻居蒂亚女士的帮助下,拿到奖学金,终于走出如同监狱般的大宅,即将重启因家境贫困而中断多年的学校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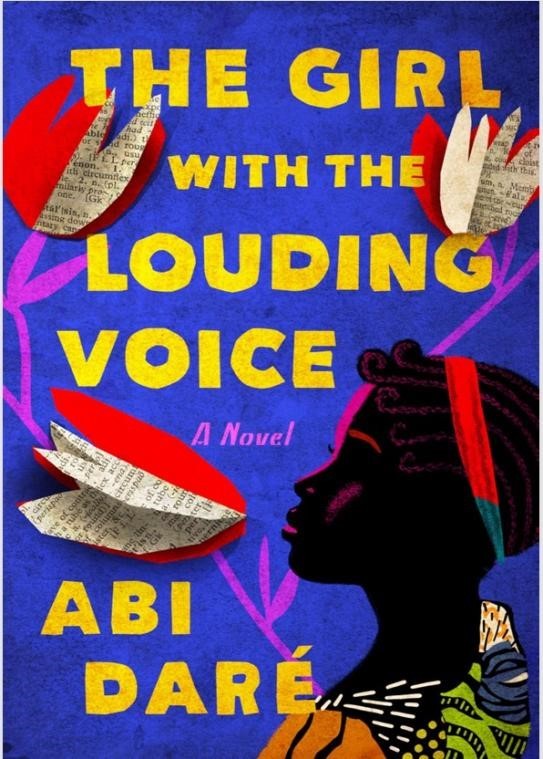
《大声说话的女孩》英文版封面

《大声说话的女孩》中文版封面
《故我咆哮》则以帮助阿杜尼获得奖学金的蒂亚女士和自己母亲之间的矛盾书写作为小说的开始。蒂亚就职于环境公司,是一位环保主义者。她对环境污染、森林砍伐和臭氧层空洞问题十分关注。
如作者达蕾在获奖感言中所说,开始写作这部小说时,她并非想要聚焦气候变化问题,而是更关注尼日利亚乡村女性的生存困境。但写着写着,她发现“实际上在非洲很多地区,气候非正义问题远比我们理解到的更严重”(达蕾的获奖感言, https://climatefictionprize.co.uk/abi-dare-acceptance-speech/)。
原本以为可以顺利开启学校生活的阿杜尼,被村长和人贩科拉强迫带回伊卡迪村。因为伊卡迪村已经数月不下雨,周围的河流渐趋干涸。于是村中决定在月满之日施行传统仪式,审判谋杀犯和小偷(当晚只审判女性),并将谋杀者丢入河中作为献给雨神的祭品。在伊卡迪村人看来,这些罪恶的女性触怒了雨神,如不尽快审判并杀死她们,干旱问题会继续恶化以致村子附近所有的河流完全干涸。
在这里女性被当作环境恶化的替罪羊。殊不知,村民们肆意砍伐树木而造成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才是干旱问题的根本原因。小说通过伊卡迪村荒诞的典仪批判了尼日利亚乡村的村民对气候问题的误解,对环境科学的无知,以及将女性污名化的传统精神痼疾。女性和尼日利亚的土地一样遭受压迫和剥削,是这个非洲国家环境政治和性别政治的交叉问题。
气候变化作为一种隐形叙事进程,与小说人物阿杜尼的人生故事、蒂亚与丈夫的感情纠葛以及阿杜尼母亲伊多乌的爱情悲剧缠绕交织。小说通过不断转换叙述视角,分别从阿杜尼、蒂亚和伊多乌的忘年交朋友伊娅的视角,讲述多位尼日利亚女性的故事:阿杜尼、蒂亚、伊多乌、伊娅、蒂亚的母亲以及被审判的多名无辜女性的生存境遇。干旱问题既是小说故事发生的重要背景,也是驱动故事情节的重要动因。村人将“女性罪恶”指责为环境恶化的主因,增强了小说中审判与反审判间的张力,以及女性与男权体制间的张力。气候变化既是重要的叙事线索,又是一剂催化药,激发矛盾张力的同时也给小说中的女性带来精神的成长,使她们逐渐认识到村人将环境恶化与女性犯罪联系在一起的荒诞性,从而激发出女性共同体内部的团结抵抗力量。
在17世纪末的美国新英格兰萨勒姆镇,曾发生过骇人听闻的萨勒姆女巫审判案。清教徒大法官将诸多无辜女性送上绞刑台,以至于“猎巫”(witch hunt)在当代被视作压迫和残害无辜人士的代名词。在尼日利亚,直至21世纪的今天,有些地方仍然保留着童婚制、童工制和各种迫害性宗教典仪。女性被视作生育工具,男方的聘礼甚至成为女孩原生家庭生活的主要物质保障。男人可以同时拥有好几个妻子,但妻子绝对只能忠诚于自己唯一的丈夫。如若某对夫妻不育,人们首先会认为是女方的问题,并通过各种宗教典仪驱除女性身上的不育恶魔。《故我咆哮》的第一章中就提到在《大声说话的女孩》中具体描写的场景:蒂亚女士被婆婆逼迫,参加驱除不孕恶魔的典仪。原以为只是一个类似于受洗的仪式,只是在河里洗浴一下身体,实际上巫师们对蒂亚实施了残酷的鞭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对蒂亚强制实施鞭刑之后,她的丈夫终于坦白,是因为他的不育导致蒂亚无法怀孕,而他一直向所有的人隐瞒了这个事实。

凯特·肖邦(Kate Chopin)
这样的戏剧反讽与美国南方女作家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短篇小说《戴西蕾的宝贝》(Désirée’s Baby,1893)中的故事异曲同工。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种族主义盛行。年轻的奥比格尼和戴西蕾一见钟情,然而他们却生出了一个肤色不纯的男孩。奥比格尼于是一反常态,变得对戴西蕾冷淡又无情,因为他觉得由于戴西蕾是瓦蒙德夫人领养的女儿,很有可能携带了黑人基因。戴西蕾心灰意冷,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亦可能是自杀)。最终,奥比格尼从母亲多年前写给父亲的信中得知,原来她是黑人,也就是说,奥比格尼自己才是混血儿。
如阿杜尼在《故我咆哮》中所控诉的:“我们的土地在流血。我们的世界在流血。而我们女孩子却承受着最深重的苦难。”这种女性替罪羊心理机制是跨越大洋的精神弊病,无论是社会堕落、不孕不育抑或环境退化,女性均被视作不幸或罪恶的源头。事实上承受最大苦难的人群便是女性。正如小说中阿杜尼所指出的,全世界都在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我们伊卡迪村受难最深重”。全球北方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但受全球变暖影响最大的是全球南方贫穷而缺乏应对气候变化资源的国家和地区。而气候变化又和全球南方地区原有的性别政治交织,加剧了性别不平等。像阿杜尼这样的广大全球南方女性,不但要和男性一样承受全球变暖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还要为很多问题“背锅”,构成一种性别和生态的双重压迫。尼日利亚乡村猎巫和女性的受难成为气候变化对全球南方深重影响的缩影。
尼日利亚位于非洲西部撒哈拉沙漠以南,是非洲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在尼日利亚北部和西南部,人们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占全国信教人口约50%。受过教育的尼日利亚人一般实行一夫一妻制,但“穆斯林和因循保守者仍然实行一夫多妻制”(托因·法洛拉著,沐涛译,《尼日利亚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7页)。1914年,英国在尼日利亚建立了现代政体,但尼日利亚诸多民族在此定居的时间可追溯至公元前500年。豪萨族、约鲁巴族和伊格博族是最大的三个民族,其中,约鲁巴族占全国总人口的约20%,主要居住在尼日利亚西南部萨赫勒草原与热带雨林地带,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主要谋生手段。英语是尼日利亚官方语言,本地语言与英语混合而成的皮钦语也被广泛使用。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虽然国内各民族之间争斗不断,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尼日利亚经济发展迅速,一度成为“非洲的代言人”。当然,贫穷和政局动荡仍然是困扰这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原因。在经济发展的背后,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
包括撒哈拉沙漠的扩张、土壤的盐碱化、城市的贫民窟、石油污染、来自欧洲的有毒垃圾在沿海地区的非法倾倒等。对热带草原上的树木肆意砍伐导致了土壤的盐碱化,而这反过来又推动了沙漠化。世界银行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尼日利亚在20世纪中森林面积缩减了90%,且每年仍将失去35万公顷的树木。另一项报告预测,撒哈拉沙漠每年要向前推进2-3英里,将导致农业收成和财政收入减少,以及干旱。国家已启动了许多造林项目[......]而对柴火和家畜饲料的需求是这些项目实施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托因·法洛拉著,沐涛译,《尼日利亚史》,第4页)

尼日利亚的地理位置
小说作者达蕾借阿杜尼之口暗示:尼日利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国家会受到全球变暖的巨大影响,而不同性别的人群所遭受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女性以及各类弱势人群面临的气候非正义问题最严重。人们砍树,开采石油售卖到国外,大量地使用木柴作为燃料,这无异于“榨取我们土地的血液”。小说中,女孩子们等待审判的森林提供了一种森林逻辑(Circle of Forest):曾是树木、鸟类和很多动物的家园的森林被人们砍伐殆尽,“犹如头发被理发师野蛮地剃除”,现在则变成了“空空的土地”和“扬尘的山谷”。所以,阿杜尼发出了“大大的吼声”,呼吁这些被审判的女孩清醒地认识到环境恶化不是她们的错,而是所有破坏森林生态的人的错,而现在女孩们应该团结起来,反抗荒诞的审判,共同帮助森林恢复原有的平衡和生机。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干旱问题的办法。
尼日利亚文学源远流长,成果丰硕,涌现出阿契贝、索因卡和阿迪契等多位世界知名作家,其中索因卡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非洲首位获诺奖的作家。当代女作家达蕾的《故我咆哮》获得首届长篇气候小说大奖,预示未来全球气候小说发展的四大方向:
一是对欧美中心主义的解构。已有的气候小说虽大多源自全球北方,但如今世界读者越发关注来自全球南方作家的气候小说作品。
二是对气候小说文类的重新界定。气候小说会超越推想小说、科幻小说以及(后)启示录小说等类型文学的边界(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5/mar/21/the-guardian-view-on-climate-fiction-no-longer-the-stuff-of-sci-fi),像《故我咆哮》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同样可以表征和反思气候变化。
三是对气候小说悲观情感面向的反拨。气候小说不会仅仅停留在描摹人物对未来气候风险的担忧与恐慌上,而是可以给读者带来更多缓解气候危机的希望和力量。
四是对气候变化叙事方式的创新。气候小说或将超越灾难叙事的修辞逻辑,将气候变化与全球及地方生态、性别政治、阶级矛盾和种族差异的历史与现实融汇,绘制全球变暖语境中的日常生活图景。
附:
英国海伊文学节(Hay Festival)首届长篇气候小说大奖的短名单:
The Ministry of Time by Kaliane Bradley (Sceptre, Hodder)
And So I Roar by Abi Daré (Sceptre, Hodder)
Briefly Very Beautiful by Roz Dineen (Bloomsbury Circus)
Orbital by Samantha Harvey (Jonathan Cape, PRH)
The Morningside by Téa Obreht (W&N, Orion)

英国海伊文学节(Hay Festival)首届长篇气候小说大奖短名单作品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