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兰与梅花的美丽邂逅,将为中国戏剧史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首次落地上海,不仅是一次奖项地理位置的迁移,更是一场艺术理念的回归与创新。

15名梅花表演奖获奖演员合影。 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梅花奖的突破与革新:回归艺术本体,书写时代篇章
本届梅花奖以“人民性”为内核,以“破局”为姿态,展现出几大特色:
从“舞美大制作”到“一桌二椅”的美学回归。“让戏剧回归戏剧,舞台回归舞台”,本届梅花奖旗帜鲜明地反对“泛剧种化”、“大制作泛滥”的行业弊病。例如,乌鲁木齐秦剧团李敏凭借《焚香记》摘梅,其舞台设计以写意美学为核心,仅凭灯光与水袖的虚实结合,便将角色心理外化为视觉语言,印证了“一桌二椅”的东方美学如何在现代剧场中焕发新生。这种“以简驭繁”的创作导向,既是对中华传统戏曲“程式化”精髓的致敬,也是对观众“次想象力”的深度唤醒——正如昆曲《牡丹亭》的“游园惊梦”,无需繁复布景,仅凭演员的身段与唱腔,便能让观众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审美之旅。
人民性与“文艺两新”的破冰。“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下,本届梅花奖首次纳入民营院团参评,如台州乱弹剧团鲍陈热以《活捉三郎》亮相,其“文戏武做”的粗犷风格打破地域界限,将地方剧种推至全国视野。同时,“文化润疆”政策结出硕果,新疆演员李敏的夺梅,是“以戏为媒”促进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而澳门地区剧作家首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则标志着戏剧创作版图向更广阔的文化共同体延伸。
表演中心的再确立,打造演员与观众的共生场域。“戏剧是以演员表演为中心的艺术”,本届参评剧目尤为凸显演员的功力。上海京剧院蓝天在张园快闪中演绎《智取威虎山》,仅一分半钟的唱段便以“声、形、神”三绝点燃观众热情,证明“人保戏”的传统并未过时。而沉浸式互动体验——如观众在宛平剧院艺教老师指导下扮装亮相,则模糊了观演界限,让戏剧从“高台教化”走向“生活在场”。

李敏《焚香记》
上海戏剧土壤:海派文化的包容与创新力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上海这座“戏剧码头”以其独特的文化基因,为梅花奖提供了丰沃的生长土壤。
这是一次石库门与剧场美学的交响。本届梅花奖将张园石库门建筑群转化为“戏剧展演综合体”,快闪活动在阳台、里弄与下沉广场间流动上演,形成“建筑即舞台,市民即观众”的奇观。这种“文商旅融合”的模式,既延续了沪剧从田头山歌走向大剧场的城市化轨迹,亦呼应了海派文化“中西合璧、雅俗共赏”的特质。而宛平剧院、上海大剧院等专业场馆的现代化设施,则为《焚香记》的灯光实验、《玲珑女》的水乡意象提供了技术支撑。
这也是一次从“戏迷”到“市民美育”的升级。上海的观众既懂戏,更爱戏。数据显示,本届梅花奖17场终评演出上座率达98%,其中青年观众占比超四成。这种观剧热情,植根于上海百年戏剧传统的积淀——从20世纪沪剧“西装旗袍戏”对市民生活的真实描摹,到今日“银杏音乐会”“豫园灯会”等公共文化品牌,戏剧早已融入城市肌理。而“戏剧进校园”“名家大讲堂”等举措,更将美育从剧场延伸至社区,培育出兼具鉴赏力与参与感的观众群体。
这更是一次守正与创新创作生态的碰撞。海派戏剧的活力,在于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以沪剧为例:它既保留了田头山歌的俚俗韵味,又吸收了话剧的剧本制与电影蒙太奇手法,形成“西装旗袍戏”的独特范式。本届梅花奖中,这种“融新”精神再次彰显——如台州乱弹与交响乐团的跨界合作,或话剧《主角》以钢琴独奏打破戏剧类型边界,皆印证了上海作为“创新试验场”的包容性。

梅花奖在上海快闪活动
“浦江潮声涌,海派悠韵长”,第32届梅花奖在上海的绽放,不仅是一次奖项的落地,更是一场文化的觉醒。它让我们看到:当“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坚韧遇上“海纳百川”的胸襟,当传统美学的写意精神碰撞现代都市的创新基因,中国戏剧便能在回归本体的同时,开辟出通向未来的路径。正如那朵绽放在张园石库门的“朱鹮衔梅”,戏剧之美,终将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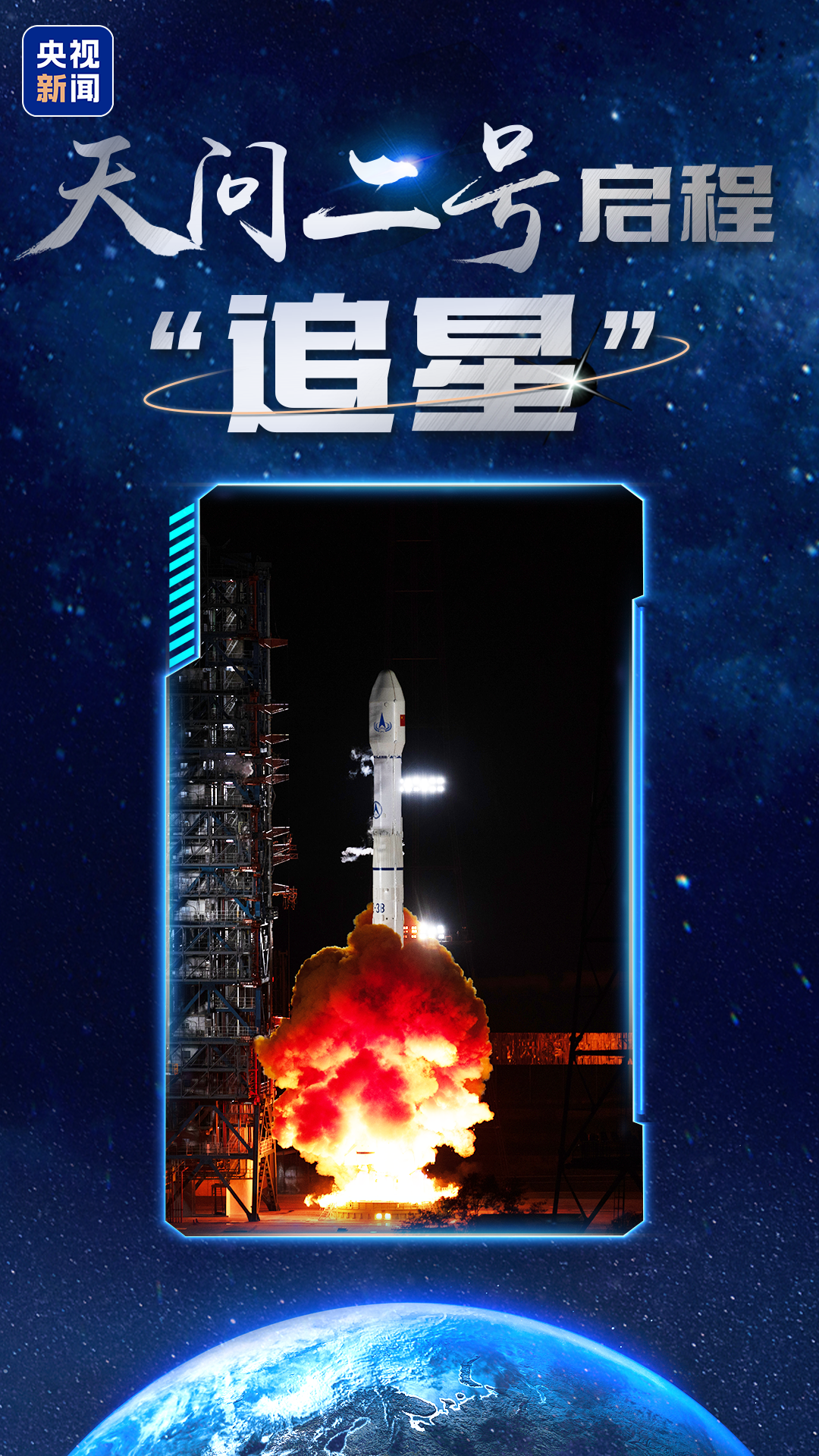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